日本新闻: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唐通事体制是清朝时期为了方便同日本进行贸易往来而设立的体制,长崎的唐通事不仅需要精通翻译汉语的工作,而且要求他们必须具备隶属德川幕府的官方身份属性。虽然这一体制在后来逐渐消亡,但是研究和整理这一群体所在的历史,对帮助我们研究日本德川政权是如何模仿中国的体制和秩序来构建自身的政权体系有着很大的作用。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在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的明朝与日本的德川政权没有直接贸易上的往来,大多都是清朝的商人独自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商业往来,直到德川政权的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期一直都是如此。在德川秀忠执政期间,日本逐渐自行构建了一套自己的贸易体系,不再想寄居在中国所主导的朝贡体系之下。到了1633年,德川政权又下令禁止日本人来往海外,1635年,中国商人同样也受到了限制,那便是商船不可以随意进行贸易,只被准许在长崎进行贸易活动。明朝灭亡后,清朝也没有与德川进行官方对话,因此暂时就默认了日本这样特殊的情况。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尽管很多人都误以为当时的清日贸易往来只是商民之间自发进行的,规则比较自由随意,但事实上,当时日方对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有具体的方针与规则,甚至是对于交易额也有限定,甚至还专设了官员负责管理与监督此事。在日本长崎与清朝的贸易往来种,日本同中国的交涉对象便是“唐通事”这一群体,他们的职务并不复杂,主要负责翻译中日语言。鲜少人知道的是,其实最初的唐通事多是中国人,因为在明末清初,不少中国人都移居到了长崎生活,这些人中不少都被选为了唐通事,不仅如此,他们的唐通事职务还可以世袭给子孙后代。据《长崎实录大成》所述,唐通事一职最初的任命者是一位叫做冯六的人,记载有言:“庆长九年(1604),唐人中名为冯六者,因通晓日本词语,故被任命为通事。”这便是唐通事一群体的由来。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但《译司统谱》及《唐通事始考》等史料中却提出了冯六这一人物为虚构的看法。而经研究发现,其实最初的唐通事并不隶属幕府的官僚体系中,他们的身份仅仅算得上是隶属民间的商人集团组织,直到1641年后,唐通事才拥有了官方编制,属于官吏。在《长崎实录大成》还详细记载了唐通事这一群体组织的设置与沿革。上述提到唐通事一职于1604年授予华人冯六,之后名为马田昌入者也被任命为唐通事,自此这个群体便由他们二人构成。在这之后,林长右卫门作为冯六的继任者上位。宽永四年,中山太郎兵卫也被认为唐通事。在随后的几年中,唐通事的队伍逐渐壮大,体制也逐步变得完善,先后细分出了大小通事、小头、唐内通事、诘番等编制。也正因如此,德川政权不仅限制了中国商船的数量和贸易额,还进一步牢固了日本对华贸易的控制,“整饬风纪、监理买卖、章程脩具”,最终日本成功地实现了“商无犯禁之弊,官有裕课之利”的局面。关于唐通事的主要编制和职务功能前文有所提及,下面笔者将对其详细的进行介绍。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第一,大通事。大通事于宽永十七年(1640年)所设,也是唐通事这一群体中,职位最高、专业能力和水平最强的群体。第二,小通事。与大通事设立的时间一样,它的存在几乎可以看作是大通事的副手。第三,稽古通事。这类通事设于承应二年(1653年),他的数量不像大小通事那样十分少,反而对于人数不加限定,因为这类通事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大小通事的后继者,所以这一群体的地位同样也很高,因为他们除了做一些辅助工作,有时大小通事人手不够,他们同样也要做一些大小通事的职务。第四,内通事。起初内通事并无官方编制,因为他们最初从事的都是一些民间翻译工作,直到宽文六年(1666年),168名内通事才拥有了官方的编制,其中的7人被任命为内通事组头,剩下的人则称为平内通事,辅助组头工作。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第五,唐人屋敷。唐人屋敷自1689年起得以建成,要求规定由3名内通事负责一艘唐船,并由1名内通事组头带领5名昼夜驻守屋敷,一共有30人,轮流驻守当差,内通事的职务做得好便有一定几率升为稽古通事。第六,唐通事目付,其主要工作为监督唐通事的日常工作,他们的权限要远远高于唐通事,设于元禄八年(1695年),最初只有两人担任此职务。唐通事目付的人选一般由退休后的大小通事中选任。第七,御用通事。御用通事大多都是由大通事来同时兼任,主要负责幕府将军订购的货物。最初的御用通事是有一名目付担任的,后来才增设一名大通事与其一起担任。在长崎担任过奉行的大冈清相曾经编纂过一本名为《崎阳群谈》的书,其中曾有记载唐船入港、交易及返航之程序等详细内容,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唐通事在清日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体工作内容。这本书中同时还记述有上缴与颁发信牌的相关内容。唐船在驶入长崎时,需要例行检查并且上收他们的信牌,并由专门人员记下船只的出发地、出发月日以及船上的具体人数等,而没有携带信牌的船只,则不准入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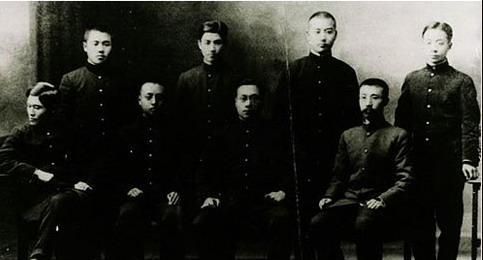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不仅如此,但凡是在日方进行贸易的唐船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日方规则,并在其所规定的文书内容上签名画押,作出保证。日方同时还有紧教条例,想要上岸的通商人员,还必须经过一道程序,那便是踩踏着绘有耶稣和圣母像的铜板,唯有如此,才能上岸。这些要求十分繁多,甚至关于唐通事如何安排唐船人员的丧葬问题也有提及,记载的十分详细。《译家必备》同样也值得参考,这本书说唐通事的语言教科书及实务手册,详细记载了中日在贸易中交易的细节和程序。尽管记载的事例多为虚拟情况,但是对于唐通事学习工作的参考和我们后人研究方面却有着极大的意义。该书中也有检查与颁发信牌的相关描述,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商船每年只有15艘被准许进港上岸,超额则不被允许。其他的关于信牌的记载与前文所提及的《崎阳群谈》基本一致,但除了这些,还记载了许多唐船交易过程中的具体内容及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唐通事不仅要负责收取唐船货册、协调处理突发事件与纠纷、还要检查是否有违禁物与走私货物;协助对唐船货物的数量、类型、质量进行评定等工作;带领中国商人前往奉行处拜见奉行,并需要纳“八朔礼”,除此之外,长崎的其他地方官员也要一一拜见;协助唐船装铜;帮助患病之人寻医问药,直至最终在唐通事的监督下送走唐船返航。《译司统谱》的编纂者颍川君平出自于唐通事世家,为其撰写序文的何礼之亦然。该书记载的是长崎唐通事的主要职能以及相关编制沿革的文献。何礼之在撰写序文时,曾经夸大信牌的意义,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唐通事所存在的意义十分深远,具有“怀柔远商,宣扬国威”的深刻内涵。要知道,何礼之的序文写于1896年,此时日本已经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取胜,因此其观点颇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但是新井白石于1715年提出的借助信牌来实现“维护国体,弘扬国威”的政治意图就十分耐人寻味了,两人之间的观点很明显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久而久之,日本的唐通事对自己存在的意义有了更加“高深”的看法。《唐通事由来书》中记载了唐通事请求改善待遇的愿望,文中曾提到“吾等按鸿胪馆之位格成为通事,唐人至今尊敬有加,成为通事老爹”。但这一观点正如李献璋所提出的质疑一样,日本唐通事已然对自己的定位进行了“神化”,在信牌制度的推行下,唐人需要严格遵守日方规定的制度,他们已经错觉般地将中日之间的正常贸易同化为中国对日本的归义与朝贡,但日本单方面的这种错觉究竟来自何处呢?《唐通事由来书》已经给出了答案,其中记载通事们在中国会馆时,唐船的船主和财副等都十分恭敬地迎送,不仅如此,结尾处还提到,在通事们的作用下,唐人得以遵从礼仪和礼法,尊重日本之“御威光”。简单来讲,“御威光”可以理解为德川政权的权威,强调的是上等身份对下等身份的威慑,也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下,中国商人与日本的通商贸易行为被强行加上了朝贡于日本的想象。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译司与唐商款约》以及很多记载中都被刻意强调了信牌对中国商人的威慑作用,当时的日本德川官方撼动不了中国本土,于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商人便成了日本可以施加权威的对象,久而久之,在日本人的心中,“日式华夷秩序”的尊卑错觉已经变成了现实,再往后,他们将对中国商人的这种看法,又强加到了中国的整个王朝之上。“怀柔远人”、“柔远怀来”这些词本是源自于中国对附属国和藩国间交涉的所用的政治修饰语,在身份位置上有很明显的上下关系,但后来却被何礼之偷换为“怀柔远商”的政治想象。在很多记载中,唐通事还扮演着“国法”、“王令”、“法纪”的角色,俨然已经成为了日本官方权威的强调者。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日本唐通事是什么样的机构?从清史入手,浅析唐通事与怀柔远商”/>
16、17世纪,由于中日官方没有直接进行往来,而处于弱势的中国商人与“神化”自身和官方地位的唐通事便为日本提供了一场自以为是的政治想象,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远远强于日本,所以日本这种高高在上的错觉尊卑思想也只是想想而已,直到近代以后,他们才将这种对外的思想强烈地表达了出来。
[日本服务器网图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